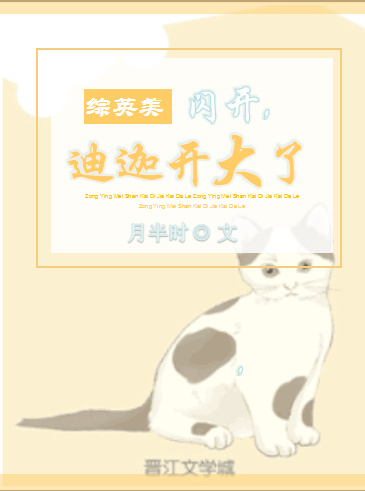书朋网>萧景珩宋昭小说免费阅读完整版 > 番外 尚阳【六】(第1页)
番外 尚阳【六】(第1页)
我当时觉得他这脾气发作得莫名其妙,许是又觉得我碍眼了?
毕竟他总是调侃,说我日日在他面前晃悠,叫他瞧着眼晕。
于是我也没去寻他,只在房中静静地整理着被他弄脏、弄皱的衣裳。
我看着那身天水碧色的常服,不知怎地,方才那股酸楚的感觉翻涌上心头更甚,不觉连带着鼻尖也跟着发酸了。
明日,
若江慕夜与哪家姑娘投了眼缘,择吉日便要离宫开府,或许这辈子我都不能再见到他。
爹爹与阿娘离世后,我每日相对最多的人就是他,
虽然他为主我为仆,但我私心里,却早就已经将他当做了最重要的人。
这天晚上,我在房中候了江慕夜一整夜,他彻夜未归。
翌日,官家女儿入了宫,也是迟迟不见他露面。
后来还是帝君下了早朝亲自来烛阴殿质问,事情闹大了,他这才姗姗来迟。
那日他与官家女儿相见我并没有跟去,后来我听说,他和蚩部的圣女十分投缘,帝君当即便敲定了他们的亲事。
自那之后,圣女顺势在宫中住下,大婚日前也可和江慕夜多多培养感情。
那段时间,江慕夜也不常回烛阴殿了。
除了政务上的忙碌,从前与我相对的闲暇时间,而今也都被他尽数挪去陪伴蚩部圣女。
我偶然在天水碧园见过他们一次,
远远瞧着他们比肩的背影,有说有笑相游漫天花雨间,俨然一对璧人。
我立在原地不敢上前叨扰,目光紧紧跟随着江慕夜,
直到他的身影随着夕阳西下一并消失在我的视线中,我的心也像是缺落了一块,被他的余影带走了。
我那时才惊觉,原来在他身边安稳的日子过久了,我竟从来都没有预想过,云泥之别的我们早晚会有分离的一日。
而这一日逐渐接近,我才明白,离了他,我大抵又要变成了无落处的浮萍。
江慕夜成婚的前夕,破天荒回了趟烛阴殿。
我见他面带喜色,许是沉溺于即将新婚的欢喜中,便掩饰好我的小心思,笑着与他打趣:
【明日成家,今儿这是回来看故地最后一眼吗?】
我这话僭越,引得一众宫人瞩目。
可一直以来,于私下我都是这么跟他说话的。
左右今日也是最后一面了,哪里还顾得上讲究那么多规矩呢?
我冒失一点,或许他便不会那样轻易就忘了我。
而他呢?
我的揶揄他并不接,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攥住了我的手腕,强势拉着我出了殿,也不知要往哪儿去。
他攥着我手腕的力道拿捏得很好,不叫我痛,也不叫我能轻易挣脱。
我只得随着他去。
我俩一路走了好远,直到入了一间早已被废弃的屋舍,他才松开我。
那屋舍从前着过火,虽没有伤着人,但瞧着不吉利也便搁置不用了。
我瞧着那里头一件摆设都没有,只在正中的地方盖着一块黑黢黢的油布,下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。
不等我疑惑开腔,他先问我:
【香云说你昨儿个哭了一夜,可是舍不得我?】
我哪里料到他能问出这样不要脸的话?
猝然闻之,不受控地红了脸,结巴地否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