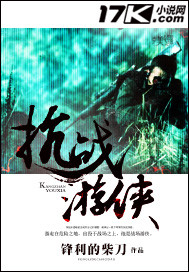书朋网>夫君宠妾灭妻,我转头嫁权臣 > 第959章(第1页)
第959章(第1页)
沈琼芝道:“是你源哥哥父亲画的。你姑父最喜欢这幅,就由着他挂在房中了。”
沈秋兰出了一会儿神,忽然叹息一声。
沈琼芝问她怎么了。
沈秋兰道:“只是心疼我那老师,虽名义上做了出家人,到底是放不下红尘俗事。听闻孙大人身子忽好忽坏的,又有一说怕是捱不到明年春日,她好几日没睡踏实,眼底下都是淡淡乌青。”
沈琼芝道:“她也是个糊涂的,都是各人命数,难过什么。心里头实在割舍不下,等他死了在自己道观里做几场法事,就算是尽心了。”
沈秋兰笑:“九姑且是豁达,老师她自己看不开,还怪你一点旧日情分都不讲呢,说也不派人去问问。”
沈琼芝道:“我派人送过药,都是管用的,再不见起色就是他自己作死。像这样的,除了阎王谁拦得住?我也没那份闲心。”
要不是惦记当年事情的真相,别说送药,她没送砒霜都算心慈。
姑侄俩说了一会儿话后,收拾沐浴换衣躺下,依偎在一块儿继续聊着。
沈琼芝见卸了妆的沈秋兰肌莹如冰,眉眼淡丽如画,又是黑鸦鸦一头好发,不禁心中感慨,摸了摸她的鬓:“初次见你时头发还有些黄黄儿的,不过一眨眼,我们兰儿就出落成这般美人了。”
沈秋兰道:“说起来都是托九姑的福,原先吃不饱睡不饱,如今天天鸡鸭鱼肉换着样子吃,头发想养不好都难。”
沈琼芝笑:“你如今在外露面不少,长得好又能干,想是有不少人倾慕。”
沈秋兰微微一笑:“倒是没有什么人倾慕我。况且见多了外头的男人,我越发只想做个女东家,潇洒快活一生。”
沈琼芝笑:“你这脾气倒是和萧霓月对上了,她也不爱拘束,跑到外头不知做些什么,至今没回来。等哪天她回来了和她商量,我出面摆桌酒,你给她做双鞋,你们认个干亲算了。”
沈秋兰欣然答应。
姑侄俩直说到夜深才睡。次日起来,她们和孙源一道用过饭,孙源去练武场温习骑射,沈秋兰则和沈琼芝一起做针线,顺带说一些铺子的事情。
沈秋兰道:“前些时我在外头遇到王大管事,见他在街上买了许多出远门要用的东西,可是九姑又要派他离京办事?”
沈琼芝道:“不是他,是他儿子。我看那孩子颇为机灵,有意栽培提拔,打算把他派到永州那边去帮手新商行的事情。”
沈秋兰楞了一下:“永州?”
永州靠近西夏,光强地旱,耕种较难,又没什么像样本地行当,虽有大片平原却是个很荒凉的地界。几个人相对最多的郡县都要死不活,只做一个往来贸易过路的歇脚处。怎么会想到去那里做生意呢?
沈琼芝道:“对,那边的棉花极好,我是想按照青州的法子把永州的新商行也弄起来,收棉花的去处和织房聚在一起,省去四面辗转工夫,本地统一打捆贩卖。”
不仅如此,她还派了人去各地重金聘请纺织高手与精密精巧织机,到时候过去教导传授共同钻研,争取早日稳定产出,打开名头。
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,是因为先前听裴玉朝提起过永州的事情。说是位置很好,是个不错的驻守之地,只可惜荒凉了些,不大留得住人。
她虽当时没说什么,却记在了心里,打算等弄起来后给他一个惊喜。
不比富贵人专用的绸缎,棉布是寻常人家也离不开的生活物资,需求量极大,算是硬通货。
如今大盛国力变强,还有夫君照看着,不用担心这生意做大了被周边盯上索要,或被上头征走,可以安安稳稳落在自家袋子里。好不容易有这样难得的条件,不认真做就可惜了。
沈琼芝明白,自己做的这么大的事不可能瞒过裴玉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