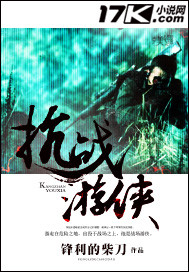书朋网>将军,嫡姐求嫁妾自请休书苏棠秦峫 > 第349章(第1页)
第349章(第1页)
秦峫到若水居的时候,母女两人都在,听下人说秦峫来了,苏夫人面露惊喜,连忙迎了出来。
“子崮来了?我就说方才这喜鹊怎么一直在叫,原来是有这样的喜事。。。。。。”
她说着吉祥话,眼眶却红了,“咱们可是许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,姨母一想到你娘早逝,就忍不住怜惜你。。。。。。”
她似是很动容,抬手擦了擦眼泪,她知道秦峫如今和苏棠正亲近,难免会听到些诋毁,对她们母女有嫌隙,所以一见面就提起了秦峫早亡的生母,她的亲姐姐罗氏,盼着如此能勾起秦峫对她们的感情。
说着话她眼角还一直在瞥秦峫,不肯放过他的丝毫情绪波动。
然而秦峫脸上并无表情,冷漠地仿佛苏夫人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
在那种眼神注视下,苏夫人有些演不下去了了,却只能硬着头皮给自己找台阶:“屋里坐吧,轻轻也在,你们先前有些误会,正可以好好解释解释。”
秦峫眼睑一垂:“昨日苏大人告诉我,说罚了她禁足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这般罚的?”
苏夫人脸一僵,没想到秦峫这般小气,竟真的和苏玉卿计较,他也不想想,苏玉卿那般病弱,若是当真禁足,要多难捱?
“。。。。。。是在禁足的,”她满心怨怼,却一个字都不敢提,只能顺着话头说了下去,“是我想起来昨天的事有些恼怒,就喊她来又教训了一顿,这就让她回去接着反省了。”
苏玉卿一直在门后听着两人说话,听苏夫人这般说,红着眼眶走了出来,哀怨又委屈地看着秦峫,却一言未发。
苏夫人怕她说错了话再得罪秦峫,连忙推着她出了院子:“你先回去装装样子,等我安抚好他,再去找你。”
苏玉卿扯着帕子,眼泪先掉了下来:“他太伤我的心了。”
苏夫人正想再安慰两句,门房忽然急匆匆跑了过来:“夫人,今天后厨的人出去采买,瞧见那将军府的管家去了济善堂。”
那间院子里有那么多秦家的下人,苏夫人不敢明目张胆的让人过去盯着,只能吩咐门房多留心他们的进出,没想到就得了这么一个消息。
“去医馆有什么好禀报的?”
苏玉卿蹙眉训斥,对门房这般小题大做很有些不满,开口就要和苏夫人道别,可一转身,却瞧见她脸色有些不对劲。
“娘,你怎么了?”
苏夫人挥挥手,将门房撵了下去,这才低声解释:“一些前尘往事罢了。。。。。。兴许是我想多了,都十几年了,哪还能记得。”
再说了,秦峫也不至于会为了这种事就来为难她。
可这话却听得苏玉卿有些不安:“母亲,是什么事啊?难道和那对母女有关?”
“你别管这些,”虽说苏夫人的确做了丧尽天良的事,可却并不想让苏玉卿知道,“快回去吧,这几天冷,你就当休养了。”
苏玉卿瘪了瘪嘴,显然十分不情愿,可还是转身走了。
苏夫人这才回头看了眼院子,深吸一口气进了正厅,秦峫正端坐在里头,丫头给他上了茶,他却动都没动一下,满脸的冷凝,仿佛索命的无偿。
饶是自己是长辈,是血亲,可苏夫人见他这幅样子,还是有些忐忑,咬了咬牙才走过去:“方才我好生教训过卿卿了,日后她必不会再被人挑唆,做这种错事。”
她耍了点心眼,试图将苏玉卿欺压姐妹的罪名摘出去,然而秦峫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,甚至连寒暄的意思都没有,等苏夫人话音落下,他单刀直入的就开了口——
“杨伯在济善堂打听到了一件往事,姨母曾在十五年前让人抓了一副十分歹毒的寒药,敢问是作何用处?”
苏夫人脸色微不可查的僵了一下,虽说她刚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可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她心口还是沉了一下,忍不住将苏棠狠狠咒骂了一顿。
过往那十五年,她竟是从来都没发现苏棠还有这种狐媚子手段,短短半年,竟然就将秦峫迷到这个地步,真的来为她们母女俩出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