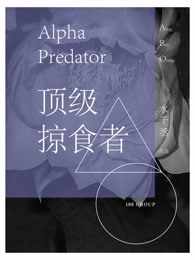书朋网>冯斯年韩如卿分手大师 > 第304章(第1页)
第304章(第1页)
我没闲着,也喝了七八杯,我低估了梅子酒的度数,会所的跟市面的梅子酒不同,后劲很上头,不辣喉却辣心,我刚出月子不敢喝冰水,嗓子火烧火燎地冒烟,我收买的女郎把段誉也灌得够呛,他第六次跑厕所的时候,我特意跟上了,在洗手间外的公共水池,倚着一堵墙喊他。
段誉从水池里抬起头,我笑靥如花在镜子里同他对视,“都说无功不受禄。我不认识段老板的公子,凭什么送天价贺礼,无非冲着段老板的面子,您收下我的大礼,是不是也要礼尚往来啊。”
酒意上涌,段誉还糊涂着,他抖落手上的水珠,“林太太与林董的新婚贺礼,我改日亲自送到索文。”
我把玩自己的指甲,“你来我往的金钱交易,那多生分啊,要不段老板还我一个人情。”
段誉浑浑噩噩问,“什么人情。”
我恢复正色,“我先生的秘书在404包厢恭候段老板。”
我讲完这句话,迅速撤离过道,防止冯斯乾疑心我们同时消失,出来打探撞见这一幕。
我再次折返包房,何江也在,他躬身对冯斯乾耳语什么,后者神情自若,可托在高脚杯底的食指却不着痕迹轻扣着,我了解他一些习惯,好歹做过俩月的贴身助理,每次爆发超出他掌控的突发状况,他都会一边思考一边心不在焉叩击物品。
他问何江,“确定吗。”
何江说,“八九不离十。”
冯斯乾目光凛冽,有极重的寒意一闪而过。
何江问,“要盯紧吗。”
冯斯乾摩挲着杯壁,好半晌,他仍旧缄默。
何江以为他没听清,拔高音量重复了一遍,“殷沛东退居二线后,从未与三教九流再来往了,这次他的司机和混混儿接触,目标必定是韩小姐,这伙人的背景很脏,不久前才刑满释放,是猥亵妇女的罪名。”
我坐在距离冯斯乾一臂间隔的角落,舞曲此起彼伏,他们对话也断断续续,不甚清晰。
小白鸭看出我没兴致玩,他和段老板的几个女郎在阴暗处黏作一团嬉闹,我更听不真切了,我没好气说,“滚出去。”
他怔住,我又骂,“耳聋了?滚。”
他先站起,几个女郎面面相觑,也纷纷离席。
很快段誉的助理走进包厢,站在酒桌前,“冯董,林太太,我们段总身体不适,接下来不便奉陪二位了,实在失礼。”
冯斯乾喝了一口酒,他没回应什么。
我说,“不碍事,段老板好好休养。”
助理离去后,冯斯乾才开口,“你干的。”
我一脸无辜茫然,“我干了什么?”
冯斯乾不紧不慢晃悠着玻璃杯,我忽然一呕,整个人前倾,匍匐在他腿上,疯狂吐着酒水,基本都吐在冯斯乾的西裤,像一大滩晕染的白墨。
何江瞠目结舌,全然忽略了及时拉开我,直到我吐完他才回过神,蹲下用餐巾纸清理着冯斯乾裤子的水渍。
冯斯乾脸上的喜怒不明朗,无动于衷看着我。
我打个酒嗝,轰然瘫软在他怀里。
他没抱住我,只任由我倒着,“她随行的秘书呢。”
何江回答,“半小时前从后门离开了。”
事实上秘书压根没离开,是故意制造离开的假象,趁冯斯乾的保镖不注意又返回四楼,在404包房等我阻截段誉。
我贸然约段誉,冯斯乾十分戒备,他比我更早清楚段誉和行长的关系,很可能也预料到我要折腾了,他一定会派人监视,所以我只有今晚的机会,争取一周之内杀他个措手不及。